
乌米饭是用乌稔树的叶汁将白米浸黑而制成。乌米饭是畲乡人的传统食品,以前畲民吃乌米饭是为了躲避恶霸掠夺而把白米染成黑米,如今制作乌米饭是为了传承畲族文化,让一个个畲乡子民时刻能够记住乡愁。
乌米饭文 · 姚增华

水美村
在那冰封雪地的塞北,就是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也算不上什么罕事。而在江南武夷山北麓,气温仅仅降低到零下时那的确也不是常有的天气。我们一行文友裹着浓浓的大雾,像似负重的甲壳虫一样,缓慢地在通往畲村水美的公路上行驶。好在半途中雾散天晴,要不这到达目的地的行车时间可能是翻倍还得翻倍。早在水美村口候着我们的雷金花大姐,见我等下车便说:“这零下两三度的天气,你们还来畲寨采风,还真是难为你们了。”

水美这村庄,坐落在武夷山北麓两支脉相夹的山沟里。那一条由南向北而流的小溪到这已经有十几里路程了,畲民们称这里为溪水的水尾。不知是山里人“水尾”和“水美”口音之误,还是笔录人的听力问题,这村庄便成了大家都已认可的水美村了。村寨人祖祖辈辈靠上山打猎砍竹伐木为生,同时还要种植少量的水田和山地。这村上现居住有五六十户人家,绝大部分青壮年人都成了或是南下,或是北上,或是东进的打工族。然而,村里的一些有识之士却不忘乡情,放弃在外乡高薪就业的机会,毅然回乡建设秀美畲乡,而本该在县城享清福的退役正处级领导雷金花,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打造畲乡文化的行列。这不,好客且平易近人的金花大姐自愿充当导游,自始至终陪同我们逛廊桥,赏畲宅,走驿道,游宗祠……还不停地给我们讲解畲寨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神话传说,并与大家一同欣赏蔡氏祠堂门口那黑乎乎的地皮菇;还有那门前屋后黄橙橙的农家柚;以及那路边山头红彤彤的野柿子等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她说畲民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自家的语言,他们对自己都称之为“山哈”,其意思就是山里人。伙伴们边听金花大姐的讲解,边品味畲乡的风光美景,不知不觉地就来到“山哈寮”的店招下,这店招字很是怪异,直观上根本就辨别不出它为何种字体,要不是落款标有“马言”二字,大家都会以为写在木板上的这三个字有可能出自小学生之手,称它为“童体”我看是最恰当不过了。金花大姐怕大家对这店招会有所误解,连忙解释这“寮”字指的是小屋,“山哈寮”就是山里人居住的地方,还补充说按照城里人时髦的说法就是“畲民之家”,并特别强调这落款“马言”就是大书画家“甘让生”的笔名。

金花大姐说,现如今畲民与汉人的衣着、饮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除了大型的庆典活动或要照相,或要录像时才正儿八经地穿戴着畲族服饰,平日里也看不出哪个是畲民,哪个是汉人。她说现在畲民已经衣食无忧了,人人都能吃上白米饭,不像从前以番薯丝为主食,或在米里掺些番薯丝,或在米里掺点玉米粒,白米饭只有招待客人时才能上席,即使是条件好的家庭也只有老的或小的才可以享受半米半番薯丝混合饭,而年轻力壮的常年也只能吃番薯丝充饥。本来畲寨的水田就少,加上山里气温又低,水稻产量自然就不高,纵然会遇上个把丰收年,也难以逃脱汉人恶霸的抢劫,要想多吃上几餐白米饭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年三月初三,畲民们聚集在一起却凑到了一个好办法,把一种叫乌稔树的叶汁将白米浸黑,给恶霸汉人来了一个迷魂阵,让刁钻的恶霸看见大米全是乌黑乌黑的,就会以为黑米有毒而不敢再去掠夺畲民的粮食,从此畲民也只能过着食用乌米饭的生活。如今这里的畲民还留有三月三过“乌饭节”的习俗,这天家家户户都要上山采集乌稔树叶,用叶汁浸泡大米做“乌米饭”吃。
在深秋初冬季节上山砍柴放牛,是我等儿时伙伴最为快活的时光。我们找茶籽桃,摘猫耳朵,采吉莲籽,吃阳甜籽……那长在茶籽树上白白的桃子,仔细一看白里还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红,可把它塞进嘴里就像似吃棉花一样软软的,有着一种清香且带有一丝丝的甜味,不过这茶籽桃也的确不易找到,就是一个秋冬季节,我们这些天天上山砍柴放牛的小伙伴也难遇到一两次,要是谁能遇上并品尝过一次茶籽桃,这味儿准能会伴他到老。那猫耳朵也不算好找,可比起茶籽桃来说那就要好找多了,其实它就是深秋时长出的茶籽树叶,这叶子白中透青长得厚厚的,咬着这软中带脆的猫耳朵也能尝到一丁点甜头。而吉莲籽阳甜籽就多了,在老家那矮矮的小山包上随处可见,那吉莲籽也好阳甜籽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汁多味甜,而我更喜欢的是阳甜籽,它不像吉莲籽那样吃了满嘴甚至满脸都会弄得乌漆墨黑的,吃阳甜籽仅仅就嘴唇边能见到一点点黑,不过有这一丁点黑已经足够让弟弟妹妹羡慕了。阳甜籽老家人叫它乌米饭,可大家更喜欢称它为阳甜籽,今天听了金花大姐的一大堆的讲解,让我知悉儿时吃的野果乌米饭不同于畲民那真正意义上的那乌米饭。
我们顺着“山哈寮”木头玛门下的坡道向上前行,只需十几二十步就能看到一栋六榀的木质瓦屋,走廊上挂满了款式不一的红色灯笼。门前有一块好大好大的平地,畲乡人称这平地为禾基,禾基正中摆放着一口硕大的瓷瓦水缸,水缸里盛满了水并栽有睡莲,金花大姐说夏天若睡莲开了,这口水缸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盆景。平日里这水缸盛满水一来可以防火,二来还可以辟……金花大姐吱吱呜呜地没有继续讲下去,她说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面前,没必要讲透你们也能知其意。我接过金花大姐的话茬“没关系的,大家也不会认为这就是迷信,说不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过这水面照一照还真得会产生一定的意外效应,到那时还要说这就是科学呢。”当然,在场的人都知道金花大姐剩下话语的意思,也知道我的话纯粹属于调侃式的玩笑话。

饭局时间到了,我们就在这畲民之家“山哈寮”用午餐,我等邀请金花大姐一同就座,而她却以要帮助打理再次推托。一会儿,一碗畲寨溪鱼上来了;接着又一碗畲山水笋上来了;紧接着一碗畲乡豆腐上来了;尔后一大碗畲菇又上来了……也就十几二十筒烟的工夫,一张大圆桌上就摆满了地地道道的十多道畲乡菜,伙伴们尝尝这道菜说地道,又尝尝那道菜讲够味,一个劲地夹菜,一个劲地品尝,只知道这菜够土够味的。金花大姐来了,她还没进包厢就能听见她的声音“到我们畲寨来没什么好吃的,鱼是圳沟里的小鱼,菇是山上的香菇,菜是菜园里的蔬菜,不知这土里土气烧出来的菜是否合大家的口味?”这时大姐把托盘中一小草篓一小草篓的食品已依次分发给文友们了,并说这小草篓里的食品叫“乌米饭”,吃起来甜丝丝且带有一定的粘稠度,大家都嫌这小草篓太小而没多装一点乌米饭。别看这小草篓小,可它的高度也约莫有七八公分,底部属边长大约为五六公分的正方形,全用一种席草编织而成,到了上半部分收口处已经却是圆形了,畲乡人称它为小草篓,专用它来蒸乌米饭。金花大姐说蒸乌米饭也不算是难事,只要把浸透的黑米拌些许蜂蜜放进小草篓里,然后在黑米上面放一颗大红枣,再把小草篓放进蒸笼里在柴火灶上蒸它二十几分钟就行了。后来,我还特意问过金花大姐,这大红枣到底有何用意,她说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在这小草篓里放一个大红枣就是在乌米饭上增加一点喜庆的色调,另外黑米蜂蜜枣子混合在一起煮熟,这也应该是一种补脾健胃的好食品。

( 柯援生 摄 )
握别金花大姐时我从喉咙里蹦出了“过些日子,还要再来尝尝这里的乌米饭!”这样一句话,大姐有点激动地说“这乌米饭是畲乡人的传统食品,以前畲民吃乌米饭是为了躲避恶霸掠夺而把白米染成黑米,如今制作乌米饭是为了传承畲族文化,让一个个畲乡子民时刻能够记住乡愁,你等能再来畲乡随时都会受到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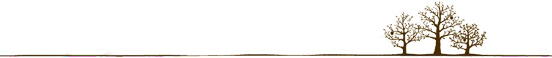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姚增华,男,汉族,江西省作协会员、铅山县作协主席、《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常有作品在省市以上刊物发表。




请输入验证码